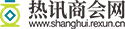十八站驿园。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十八站北驿路口。
古驿路在黑龙江省境内有千余里,驿站遗址33处。我花了6个小时,在大兴安岭地区塔河县境内观光古驿站,算是对古驿线路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唐初大学士褚亮有诗云:“浮光随日度,漾影逐波深。”在悠长的古驿路上,我的文字仅为走马观花之笔。
十八站小镇风貌
车出塔河,沿着镇北高架桥驶过。经永安,过塔丰,走永庆,顺着窄窄的沥青公路,爬坡甩弯地向十八站驶去。
十八站是1685 年,在嫩江上游至大兴安岭设立的 25 个驿站中的第十八个。数百年里,十八站,这个驿站骄子硬是从苍凉中走了出来。大兴安岭开发建设后,十八站被定为鄂伦春民族乡和林业局并用的驻地,逐渐成为一个社会功能健全的小镇。上世纪80 年代末,我曾作为县委工作组成员到此进行调研。那时的十八站,民族乡在南,林业局在北。当时,乡里和林业局的第三产业都不发达,生产经营主要还是靠卖木材。初次来时,当地群众的生活水平还算不错,可居住的条件却很差。一栋栋板夹泥房,在砂石路两侧冒着缕缕炊烟,生活单调枯燥。两年后再来此地,板夹泥房变成了砖瓦房, 也平添了几栋楼房。原有的砂石路,变成了能并排跑两辆车的水泥路。当然,两次来此地吸引我的,不是这里的民居和小镇风貌,而是独特的驿路传说和民族文化。
40 分钟后,我们到了十八站。把车停靠在十八站入口右侧的遗址处。我早听说这个遗址,初到十八站时就曾到此参观过,只因当时年轻, 缺少些深刻的感悟罢了。遗址位于呼玛河北岸不远处近 20 米高的平台上。近百平方米的遗址上比原来多了一圈铁栅栏,新涂的漆刚刚干,近闻还有些刺鼻。大兴安岭开发后,国家考古队曾先后两次到此考察,先后在此处及十八站以西 3.5 公里、以东南 5 公里处发现三处遗址,出土了很多稀奇的石器。刮削器、尖状器、石叶、石片和石核等,收获颇丰,考察证明:这些石器距今达12000 年。器形、风格、大小等,都与北京周口店出土的石器相似。考古队如获至宝,兴奋得不得了。后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将十八站旧石器文化遗址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兴安自古不荒凉
1982 年 6 月,在十八站 3 个遗址处分别立了高 1.4 米、宽 0.9 米、厚 0.12 米的石碑。碑上都竖刻着: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十八站遗址。
石碑自然还是 1982 年时立着的那块儿石碑,字体古朴凝重,苍劲有力。背面刻着的百余字,却因风侵雨蚀,早已斑驳模糊。碑文刻着的内容主要是对遗址的发现、挖掘时间以及出土文物的件数和挖掘的重要意义进行了扼要叙述。十八站遗址的发现,轰动了国内外考古界。大兴安岭远古时期再也不是旷古无人的不毛之地了。早在一万多年前,大兴安岭就有了人类,而且已成群居规模。立石碑时,一位当地领导讲解发现遗址的意义,并建议加大宣传报道,让更多人知道:大兴安岭绝非苦寒之地,更非自古荒凉没有人烟。
我手扶石碑端详,除了碑文模糊外,碑体也有些老旧。40 多年前立的,当然有其局限性。那一道道山岭,还有一片片树林苍翠绵延。远古文明是一笔宝贵财富,也是大兴安岭宝贵的历史。大兴安岭不仅有自然资源,还有一代又一代敢于探索勇于发现的探索者。
乡政府还是一栋平房,似无大变化,只是几经修缮,门脸变得耐看了。感慨之余,我和当地几位朋友在大门前合了影。当年来此调研,连个吃饭的地方都没有,好在离林业局食堂不算太远,赖着脸填饱了肚子。
依山傍林的公园
驿园是十八站林业局精心打造的一个开放式公园。大门前立着高大的牌楼,正中有蓝底金色两个大字“驿园”。大门两侧各筑有一只石狮子。驿园是十八站林业局的文化名片。当地一位朋友说,这几天林业局正筹备鄂伦春民俗文化节呢,届时这里将成为开幕式的主场地。驿园里除了“龙蛇狮龟背驮”的驿路文化符号外,还建有长廊和亭台。吸引我的,倒不是这些景观,而是长廊前的地上绘制的驿站图。
大兴安岭的公园, 多依山傍林,即便地势平坦,那树木也一定要茂盛。驿园生长着俊美的樟子松。我对樟子松情有独钟,不仅因其高大挺拔、葱郁苍翠,更是因此树有着一种顽强的精神。我欣赏着,感叹着。驿园里的樟子松,不就是古驿路上千株万棵樟子松的缩写吗?樟子松不愧是精神之树。
在十八站北出口,我被路两侧的景观吸引。路口西侧是形体各异、排列整齐、高不过两米的“驿”字碑林。这些“驿”字,都是古今名人所书的传拓之本。拓印字体涵盖篆体、行楷、隶书和魏碑等。放眼望去,碑林“驿”字铁画银钩,苍劲有力。有的龙飞凤舞,有的娟秀光丽。路口东侧建有驿站门楼及驿路呈祥和人物雕像。原木搭建的门楼挂满了红灯笼,远远望去,一派喜庆。遥想当年驿站,一盏灯火幽幽暗暗,闪着清冷的灯火, 该是何等孤寂。长阶缓缓,驿站门楼似在遥望,又似在古驿路上追忆苍凉。朋友问我要不要登门楼而观风景,我摇头。不用上去,我也知道四周的风景一定是美的。
门楼前一座垒砌的石碑,上面拓着康熙的御笔:驿路。字体风格雍容,笔力刚强,如苍岭劲松,傲然耸立。康熙竭力开发驿路, 确保边疆长治久安。能每隔 30 公里依序设立驿站,直到当时沙俄临界的黑龙江边,其捍卫疆域的决心可见一斑。斯时,大兴安岭东部林木苦寒,人烟稀少,何谈安宁与发展?门楼前的石碑端正大气,而路两侧的古铜色塑像则栩栩如生。一侧:一名站兵往马槽子里倒草料,一名则在骏马后几步远的地方举起马鞍子,准备往马背上搁。另一侧:两个挎刀的站兵,一名骑在马上,回头与另一名立于原地的站兵挥手告别。那马已踏蹄欲奔。就要出发了,就要向下一个驿路疾行。在他们两个中间,筑着 3米来高的石垒方印,上面闪着古朴的光:黄金之路十八驿站。